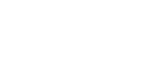《我是刑警》编剧徐萌:流量时代现实主义叙事破局之道
2025年4月24日,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首都视听产业协会主办,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北京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联合主办的2025首都视听节目春交会在北京郎园Station中央车站盛大开幕,活动以“合见未来・光启新篇”为主题,聚焦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一级编剧、制片人徐萌受邀发表“极致输出与极致体验:流量时代的现实主义叙事策略”主题演讲,她结合《我是刑警》的创作经验,分享流量时代现实主义题材的叙事革新思路。
徐萌深耕影视行业三十余年,代表作《医者仁心》《我是刑警》,曾获飞天奖优秀编剧奖,以职业写实风格著称。她在论坛中提出,流量时代创作者需以“极致输出”实现“极致体验”,通过贴近现实的叙事策略突破传播壁垒,让主旋律内容在碎片化环境中触达观众。

以下为演讲全文:
弱传播与流量时代逻辑:时代变了
流量时代,任何行为包括艺术创作都是舆论场的一部分。一部剧如果想引起关注、出圈,除了自身的质量,必须经得起舆论场的议论与冲击。
厦门大学邹振东教授的《弱传播》一书,讲到弱传播理论,揭示了社交媒体时代的生态和传播特性,简单说就是谁弱谁有理。
“人类生活在现实世界与舆论世界这两个世界,前者是强世界,后者是弱世界。”
“舆论世界的强弱与现实世界的强弱刚好倒置,通俗地表达就是:现实中的强势群体就是舆论中的弱势群体。现实中的强者要在舆论中获得优势必须与弱者相连接,必须从弱者中汲取舆论的能量。”简单说就是学会示弱,以“弱”者的立场讲故事。
这种强还是连接的强,比如朋友圈是强媒体,因为它是实名的。而弱的属性还来自于匿名,匿名导致表达更接近人的原始真实心态和群体的非理性。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表达的自由,下沉市场基数大,其认知水平决定了传播以情绪为主,谁人多声大,舆论表面的导向就会偏向谁,传统世界的声音被压制。现实世界里高位者、官方的、上位者往往容易被忽略,大众天然就有这种区分能力,快速分辨出强弱,官方的强过民间的、男性强于女性、年长的强于年幼的,在你意想不到的任何地方都会被区分出来,然后翻车,这是近年来舆论场的常态。
在认知传播里,事实最重要,在价值传播里,是非最重要。在故事传播里,恩怨最重要。人们往往来不及看完整的事实,就想直接知道谁对谁错。人们往往不在意谁对谁错,而被恩恩怨怨吸引。
这是人类的可悲之处,也是人性最真实的表现。
每天数以亿计的视频流从人们指间、眼前滑过,停留时间越来越短,观众要看的东西越来越刺激。除了追求惊悚、刺激,其实是某种触动,陌生、感动以及对世界、人性边界无限的探索。人们一面把自己代入受害者,同时又希望对恶的边界不断探求,追求高烈度的对抗,凡是官方的,正面的、正向的输出非常不容易打响。人们忙着追逐与自己好恶与情绪相关的事件,卖惨、喊冤、诉苦、维权、站队、撕扯,传统世界里被视为常识的东西,舆论场上都能吵得不亦乐乎。加上饭圈、饭圈式的产品营销,在一次次的撕扯、反转、造神与弑神的迭进中,争夺关注与流量,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世界运行的逻辑变了,我们舆论场很难发出声音。而关注力是稀缺资源,我们正面临关注力集体缺失的困境
《我是刑警》的叙事策略
在这样的生态下,回头看《我是刑警》做对了什么。

经历了八个月的采访,采访了两百多位一线刑警,我们对刑侦行业强烈的印象就是,刑警队伍已经完成升级迭代,精明强干,智力超群。和平年代,社会治理,警察的智力、办案水平、现代技术水平的高低就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我们有自己的神探、刑侦八虎,技术大拿,有国宝级、泰斗级的人物乌老崔老。而他们真实处境的则是:破案没有金手指,没有上帝视角,每个案子靠的都是摸排,以前是人力,现在是监控、大数据四件套,背后都是难以想象的付出。
于是我们开始寻找矛盾点、强弱对比点:虽然警察看上去是强势的,但面对犯罪份子的凶恶,面对错综复杂的案情,面对未知和不确定性,犯罪份子是强势的,警察其实是弱势。他们破案靠手工作业人力摸排,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威风八面,所以,我们就坚定了就写出刑警真实的工作与生存状态,写出他们的艰辛与磨难。
现实主义出大剧
很多人认为,这个剧中的案子看上去如此真实,是编剧一开始就拿到了一手资料负责改编就行了,其实不是。真实案件其实是没有调性的,案件各个元素,从犯罪嫌疑人到作案手段、作案动机到受害人、受害人家属,甚至一个路人,都有视角,每个视角扯开都是一种叙事逻辑和叙事方式,这就是我们看到各种犯罪题材不断出新,叙事不断迭代吸引观众追看的原因。但老实说,一部戏真正想立住,成为伟大的作品,引起普遍的共鸣,现实主义风格手法是惟一的出路,它也是最难的。而真实,是制胜的法宝。
极致输出:
比真实更真实的是逻辑的真实
确定了现实主义风格,我们开始寻找“爆”点,今天的观众,对什么样的故事都不稀奇了,他们要看的是故事里真实的人,要看最真实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同样,他们渴望得到认知上的提升。2008年开始,DNA、视频、技侦、网侦四大技术的全面应用,使刑侦工作飞速发展,命案破案率到了99%以上,但新四大技术对诉讼证据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也让行业在自我更新中重置与重生,这对行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于是我们找到了这个剧最根本的逻辑:在行业发展的大结构中找到矛盾点与痛点构建事件与冲突,我们相信行业大逻辑的真实能让作品充满时代感与专业性,观众一定会喜欢看的。于是沿着这个逻辑,人物、故事都被设置出来了,案件也要为主题和人物服务,通过这些案例展示刑侦发展的历程,走向信息化、科技化、规范化的艰难历程。
极致输出:伟大与残酷
我们当然知道观众希望在一部刑侦剧看到什么,就是高烈度的对抗、现实的残酷,所以我们选择了几个大案重案,让观众看到了“128”大案中犯罪分子的凶残,灭绝人性,张克寒的极致狡猾与极致凶残,当然更重要的是秦川与战友极致的坚持。
同时我们适度展现了公安内部本位主义,在张克寒案中配合一次次失误,这不是为了揭密制造矛盾,而是为了催生新的现代化指挥系统。
我们又选择陶维志这样一个“反故事”,展示在刑警这一需要终身学习的行业里,新旧更替的残酷性。我见到过原型本人,多年过去了,他依然处在应激状态,滔滔不绝可以说上三个小时。五年的时间里,他和他的三人疯魔小组翻山越岭却与真相背道而驰,偶尔柳暗花明却总是差临门一脚,看似掉进案情中,其实是掉进新技术的汪洋大海。当真相最终降临,人们都奔赴了新的战场,他却被失败感和记忆钉死在原地。
这些故事、情节既残酷又伟大,就是这些人几十年、三代人的艰苦奋斗与传承,奋斗与磨难交织,让中国成为最安全的国家,让老百姓有安全感。今天,DNA技术全面成熟,大数据、人脸识别、各种高科技,对国家的现代化治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非常感激观众对《我是刑警的》喜爱与支持,他们认出了这部戏。我也要感谢广电总局领导、中央广播影视总台、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和制片人郭现春先生、爱奇艺、华策集团赵依芳总裁、傅斌星总经理以及宽厚影视总经理制片人徐颐乐女士对我们无条件的信任与支持,这部剧真的是凝聚了太多人的心血,也惊动了太多的人。我想向各位分享我在微博上看到的两段评论,观众的惺惺相惜,是对创作者最好的褒扬。
@巴别塔2519:“我看着看着就会鼻子发酸的想哭,具体为什么哭也说不清,想了一会儿想明白了,就是电视剧还原度很高,我感觉看到了我的故乡,东北三省的一个三线小城市,看到了记忆里了那些人,那些事……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的乡愁。”
网友感慨,“如今敢深夜走在街头,千言万语,感谢艰辛付出,感谢时代进步,英雄的崇高感接了地气,观众的安全感得以兑现。”
接纳大千世界、把根扎得更深一些
编剧其实是个粗鲁凶悍的职业,手持利剑,生杀予夺。我们其实一直都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也会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生活在玻璃鱼缸里。
面对时代的急剧变革,面对新的生态,我们要走出去,沉下去。那么多短视频自媒体、平台的弹幕观众每时每刻都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内心,真实的生活状态、趣味、喜怒哀乐,让我们看到一个多元的、生动的、蓬勃的,同时又光怪陆离、五彩斑斓的世界,这是最宝贵的生命体验。所以接纳大千世界,把根扎得更深 一些。生活没有那么复杂,所以要学会直接、干脆、本质的表达,这是叙事的根本,也是艺术的根本。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艺术理想,守住善良正直的边界和底线,守护我们的时代,与时代共生。